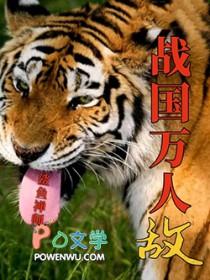嗨呦小说>手术刀和吉他弦 > 第114章(第2页)
第114章(第2页)
第二天醒来,楚琅只觉得浑身酸痛,像被人卸掉了四肢,连翻身都翻不利索。她强撑着睁开酸胀的眼皮——毕竟她昨晚连三个小时都没睡够。
何谦鸢不在身侧,却能听到客厅里轻轻翻动纸张的声音。她想唤他,嗓子却哑到失了声,刚想拿起床头的水杯,手指却脱力没握稳,碎落在地。
何谦鸢冲刺着跑进屋,“怎么了?”
楚琅看到他的脸,突然莫名慌忙地缩到了被子里。
何谦鸢大坏蛋!
何谦鸢过来看到了一地的玻璃碎片,还以为她割到了手,压根没想到她是因为害羞躲藏,一下子把被掀开:“你没伤着吧?”
看他一本正经地问自己“受没受伤”,楚琅又气又急,恨不得给他一拳。
“没有!”
何谦鸢被她吼得愣住,只能先把碎片捡起来。楚琅顺着被子的缝隙往外偷看——
何谦鸢的颈侧,有块显着的红色印迹。
安心
何谦鸢收拾好碎片,又拿拖布拖了好几遍,确保连水渍都没有了才罢休。
“别闷着了,憋得慌。”何谦鸢坐在床边,端着杯新冲好的茉莉花茶,“起来喝口水。”
楚琅死死攥住被角,带着股就要把自己憋死在里面的执着。
何谦鸢见她这个样子,无奈地笑着摇摇头,关上门出去了。
待他走后,楚琅把被猛地掀开,深吸了一大口气。
缓了好一阵儿,她突然觉得肚腹空空,一看手机,竟然都下午一点多了。
她拿起何谦鸢一早放在床尾的、和他那套情侣款式的粉色睡衣,窸窸窣窣地换上。
他好像很喜欢情侣款的配置,恨不得连家里的杯子都是。
结果她一开门,却看到他在客厅迭着衣服,面前是个打开的大行李箱。
“你要出远门嘛?”这么大一箱子,够她放一个月衣服的了。
“不是。”何谦鸢放下手头的活儿,起身扶着她到沙发坐下,关切地问:“有没有不舒服?还痛不痛?”
要不是自己不会缝东西,她高低得把他的嘴缝起来!
“没有!”她赶紧移走话题:“那你要去哪里呀?”
“羊城。”他帮她按摩着大腿酸胀的肌肉。
“羊城?你有演出么?”楚琅心里逐渐形成了个猜测,却不敢问出口。
“去见你爸妈。”何谦鸢揉了揉她凌乱的头发,“我得让这戒指,戴得心安理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