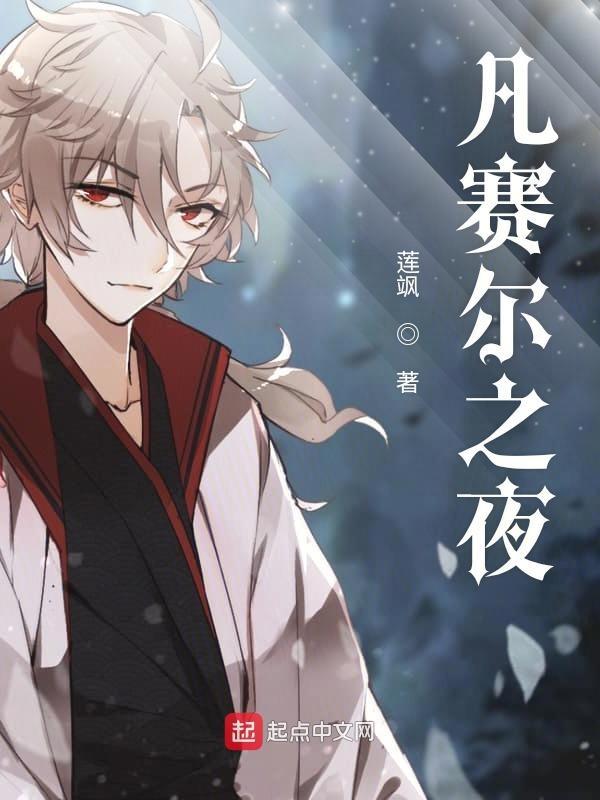嗨呦小说>大唐一根棍 > 第737章 明君长什么样(第1页)
第737章 明君长什么样(第1页)
李德裕约刘异见面的地方在安邑坊肃明观。
李德裕家就住安邑坊,他有个妹妹还在肃明观修行。
刘异在黄昏日落之时抵达肃明观。
他上次来时还是鸟语花香,现在已经草木凋零,唯一不变的三清殿里飘出的淡淡檀香。
刘异走到后院,发现李德裕已经到了。
他身穿蓝色常服,外披一件玄色大氅,正坐在光秃秃的大槐下品茗。
旁边火炉里炭火正热,熏烤得周围暖融融的。
刘异走过去坐到他对面,将两只手伸到火炉上烘烤。
“李太尉近来安好啊?”
李德裕默默凝视刘异,面带着笑意反问:
“刘街使给老夫设下了十面埋伏,你让我如何安好啊?”
“我大难不死刚回到长安,听不懂李太尉的话。”
“刘异,老夫既然约你过来便是诚心谈和,你又何必否认?”
刘异举起几案上的茶壶,给自己茶盏里倒了一杯热茶,自顾品了一口。
“诚心?不见得吧。”
“哦,老夫诚意不足吗?”
刘异扫视一圈肃明观后院,面带讥笑说道:
“让我猜猜李太尉将杀手埋伏在哪了……药圃后面草屋估计能藏几十剑手,东墙外面原来是元法寺,现在肯定已经废弃了,那边适合埋伏弓箭手,等下他们可以直接翻上东墙,再往院里射箭。”
李德裕脸上没有被戳穿诡计的尴尬,表情依然淡定从容。
“刘街使用兵如神,小小迷障自然瞒不过你的法眼,但你如今掌控着京城半数兵力,老夫总得自保啊。”
他明白刘异既然明知有埋伏还如此有恃无恐,那自己的布置大概已经无效,刘异肯定有后招。
刘异见李德裕茶杯已空,顺手给他也添了杯茶。
“李太尉此次约我前来,不单只为杀我吧?”
李德裕望着对面比自己最小的儿子还年轻的少年郎,不禁长吁一声。
“老夫一生与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首的牛党苦斗了四十多年,素来小心谨慎、步步为营,不曾想鹬蚌相争、渔翁得利,竟让你在暗中做大。等老夫察觉到朝中有人另结新党时,荥阳郑氏、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等士族已经背叛,此消彼长,新党势力已经远远超过鼎盛时期的牛党,可以与李党分庭抗礼。”
“韬光养晦偷摸成长而已,跟我家兔子学的。”
“兔子?”李德裕疑惑后嗤笑,“于老夫而言,你比牛僧孺更加危险,牛僧孺野心再大,不过想要在朝堂上与老夫争权罢了,而你却谋害天子,图谋大唐江山。”
刘异撇嘴否认:
“你言重了,我对江山对权力都不感兴趣,只不过有个很小很小的愿望。”
“什么愿望?”
“杀个皇帝而已。”
李德裕震惊于刘异轻描淡写的语气,好像在他看来杀皇帝像杀鸡鸭一样稀松平常。
“刘异,我不知道你与陛下有何恩怨,你为何一定要弑君?”
“李太尉不是曾为皇帝做媒,劝说荥阳郑氏女儿入宫为后吗?被你劝进宫的皇后是我心尖上的人,我与李瀍有夺妻之恨,而你是那助纣为虐之人。”
李德裕满脸震惊,他并不清楚郑宸与刘异的关系。
他人生的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朝廷政务与党派斗争中。